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指导,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出品的原创话剧《赵一曼》,以革命家的生命激情、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为当前一种“软绵绵的成人童话”创作倾向注入了刚健之气。该剧以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牺牲前夜作为故事原点,以赵一曼的母子情、夫妻情、战友情作为故事线索,讴歌了赵一曼在面对日军刑讯逼供时坚贞不屈的革命信仰与民族气节。《赵一曼》先后在首都剧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演,使观众获得艺术震撼与审美享受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对于“英雄”话题的广泛探讨,更引起了当代人对精神世界与价值取向的强烈反思。话剧《赵一曼》的主创者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力”与“美”抒“义”与“勇”,作品的现实意义值得彰显,其艺术感染力足以给人以启示。

话剧《赵一曼》彰显的“义”与“勇”是时代的呼唤。所谓“义”,乃是大敌当前时,不再蝇营狗苟;其“勇”,不再是个体之勇,而是升华为民族之勇。人们对赵一曼这样的民族英雄的崇敬,乃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英雄的精神礼赞。剧中,赵一曼在孩子出世不久,毅然奔赴东北投入战斗。在敌营地狱般的蹂躏中,赵一曼毅然放弃“安眠药”的解脱方式而选择以柔弱之躯抗争到底。“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民众过着物质与精神之双重悲惨生活,沦为了国无所依、族无所靠的“真正悲惨”的“精神难民”。赵一曼的革命事迹感召着剧中“贫穷、愚昧、落后、麻木”的民众,唤起了日营中的护士韩勇义与守卫董宪勋这些麻木不仁的民众,使他们获得了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皈依,这正是在国家存亡时刻民族觉醒的一种缩影。《赵一曼》中昂扬的斗志,对当下一些沉醉于物欲横流与消费盛行的“小时代”中难以自拔的国人来说,难道不足以唤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吗?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类话剧,《赵一曼》以人物推动情节,该剧采取以“同源视角”为主的多视角叙事策略。开篇设计了赵一曼在就义前夜与青春时代的另一自我的心灵对话。这一时空交流贯穿全剧,既是自我叩问、自我体悟的一种“同源叙事”与主观宣情,又是基于不同时空、不同心境下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异源叙事”与“他者观照”。如此精巧的设置不仅使人物塑造更为立体,而且使情节表达更富弹性。剧中,与赵一曼阵营形成对峙与冲突的是看似具有强大武力的日本军官大野泰治,这一凶残狡诈、野心勃勃的形象正是日本天皇军国主义之集中体现。深入剧情,创作者使用了“交替衬托”之法,准确刻画了其卑劣与野蛮。譬如,大野泰治之妻纯子听闻丈夫用竹签穿透赵一曼手指的暴行后大惊失色,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停止“卑鄙行径”。这一情节从侧面衬托出大野泰治之凶残连其至亲亦难以容忍。借助纯子这一视角,将初见大野泰治时的美好军人形象与当前对暴行夸夸其谈的恶魔形象两相对比,使不义之战如何把“人”异化为“兽”的人性泯灭过程展露得淋漓尽致。
英雄形象托举起的灵魂之美无疑是一种崇高之美。剧中,赵一曼在“时空对话”中曾说:“我说的解脱,是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意志会瓦解。在这场与日本鬼子的单兵较量中,我最终没输!”在面对严刑拷打时,赵一曼面临的所谓“单兵较量”便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具有强大武力的大野泰治的失败,更能体现只有柔弱之躯的赵一曼的伟力。不仅如此,作品还折射出了刚柔并济之美。赵一曼既有巾帼英雄铮铮铁骨的一面,也不乏东方女性温婉贤淑的一面。在那个不愿缠足、古灵精怪的四川“幺妹”身上,显露出的是孩童般的灵动与纯净;在那个月光皎洁、柔情似水的夜晚,流露出的是恋爱少女的浪漫与娇羞;在那个临危不乱、化险为夷的关头,展露出的是革命战士的机智与果敢;在那个忙里偷闲、炕头绣帽的革命母亲身上,透露出的是身为人母的依依不舍与舐犊情深。亲情、爱情、革命友情与民族大义所勾勒渲染出的是一个鲜活的、灵动的赵一曼,也使作品散发出具有东方色彩的刚柔并济之美。
当然,该剧艺术呈现方面亦有白璧微瑕之处。比如展现韩护士与董守卫协助赵一曼逃离日营,距离“抗联”仅有二十余公里处不幸被日寇截获这一情节之时,如果能够化语言叙述为舞台行动,也许更有利于营造悬念而使情节更加扣人心弦,更为形象地表现出突破日寇封锁线之艰难,从而折射出整个抗日战争之艰辛,更为深刻地展现出普通民众的意识觉醒与抗日决心。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老师)
(编辑:曹琬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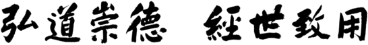
 回到顶部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