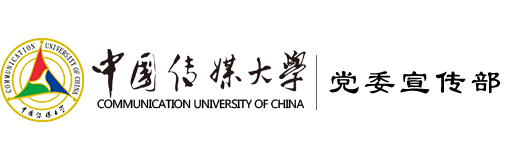不背叛电影的电影
“这个世界已经不精致了。”
——2013这一年里最卓越、最令人兴奋的外语片,竟是对一个逝去的古典时代的怀旧一瞥。《绝美之城》让世界忽然意识到:意大利电影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黄金时代,艺术电影曾是意大利电影的重要传统,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维斯康蒂等堪称欧洲艺术电影的高峰。费里尼《甜蜜的生活》作为一种现象被载入西方当代文化史,比如它是今日“狗仔队”的滥觞所在;《八部半》(1963)几乎等同于意识流与创作障碍原型。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1964)创造了影史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电影,《放大》(1966)对“真实与幻觉”的哲思先验性地预言了后现代主义;维斯康蒂《豹》(1963)中的舞会堪称影史中最盛大的一场舞会,《魂断威尼斯》(1971)惊世骇俗地追逐艺术本质并贡献出“世界第一美少年”……
如果电影世界存在着某种不平等,那么好莱坞便是隐喻意义上的文化殖民者。欧洲艺术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作为好莱坞的反面而存在,颠覆了闭合叙事与戏剧冲突。索伦蒂诺复兴的正是欧洲艺术电影传统,他实践了一种更具坚强气质的浪漫主义,不仅追随了费里尼的传统,还有诸如奥森·威尔斯等用幻想与谎言揭示被掩盖真相的智性艺术。他的电影几乎都没有一个完整故事,一切处于拆散线索、彼此交织的状态;黑色幽默的戏谑讽刺、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足以弥补所谓的传统情节的缺失;主人公的个性、人格是个谜,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暧昧与模糊,观众能够在情感上接近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在其身上投射部分的自己。
走进《绝美之城》如同走进文学沙龙:福楼拜、皮兰德娄、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索伦蒂诺的另一身份是作家,曾出版小说集《每个人的权力》。事实上,意大利电影的一大传统即文学性,意大利电影比任何民族电影都更加程度非凡得依赖文学,很难找到一个意大利电影的主题没有参考先前存在的文学文本或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威斯康蒂被誉为“最后的电影贵族”,既缘于贵族出身、亦缘于积淀深厚,文学是其艺术源头:《白夜》(1957)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豹》(1963)改编自兰佩杜萨的小说,《局外人》(1967)改编自加缪的存在主义小说,《魂断威尼斯》(1971)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小说……
今天,很多时候,市场成为新的“独裁者”。电影人急于讲述一个好卖、大卖的故事,难于专注艺术本体。而意大利电影人重新发现了意大利电影中歌剧审美与史诗叙事的魅力:与贝托鲁奇并称为意大利之李白与杜甫的老将贝罗奇奥拍制了《墨索里尼的情人》(2009),以悲怆的歌剧审美创造了一位“现代美狄亚”;新生代导演卢卡·瓜达格尼诺在《我是爱》(2009)中复兴了维斯康蒂的唯美主义古典风格,创造了一个现代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如果《豹》是古老贵族的挽歌,那么《我是爱》则是现代贵族的挽歌。意大利已经许久没有这种展示贵族奢华生活的电影了:从俄罗斯远嫁米兰纺织工业家族的女人,将自己的俄罗斯名字、身份与情感隐藏得天衣无缝,终有一天离家出走。影片有意识地营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米兰豪宅,冷调,冬季,多取广角、大景深,人物关系远;一个是尼斯乡下,也是主人公找到自由与爱的地方,暖调,夏季,以自然光、特写镜头为主,捕捉细节和亲密的人物关系。两个世界代表了秩序与自由、传统的压制与自我的苏醒。
事实上,近年欧美电影都在反思商业泛滥的窘况: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提名的《锡尔斯玛利亚的云》与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鸟人》,不约而同讽喻了大行其道的超英雄大片:艺术性缺席,严肃与深度缺席,演技非凡的成年明星纷纷滑稽地披上斗篷、戴上面具、扮成各种侠。有趣的是,没有对外国观众乃至好莱坞美学做出让步的《大牌明星》成功了,成为索伦蒂诺第一部在美国公映的电影;在《绝美之城》为奥斯卡上演“罗马人的征服”后,索伦蒂诺一举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意大利导演——2015年他集结老牌明星迈克尔·凯恩、哈维·凯特尔、简·芳达拍制了第二部英语片《年轻气盛》,迈克尔·凯恩的角色转换充满互文意义:他由《黑暗骑士》中“蝙蝠侠”的管家,变成了思考爱与欲的作曲家。
索伦蒂诺践行了自己的信条:拍不背叛电影的电影。